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欧洲一体化”的历史)
10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4-11-13 09:22:43
对欧洲一体化历史的共同理解,混淆了欧洲一体化与其在西方多边合作中的前史之间的牢固联系,这种西方合作,以欧洲一体化前阶段的货币管理、贸易和社会政策等相互关联的政策领域为中心。
这一举措重建了跨大西洋体制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战后西欧可能出现一种独特的多边主义。这是战后多边主义的欧洲变体的特征: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追求的区域导向的“社会市场”。
欧洲一体化的“起飞”并非在历史真空中实现,正是在1950年前大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多边主义,为战后欧洲一体化奠定了制度上的滋生空间。
1950年之前的多边主义建立了一个制度“实验室”,早在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发、测试和讨论了欧洲密切合作或一体化的截然不同的倡议。
1940年代初,首先是在英美合作的框架内,这个实验室逐渐发展起来,1944年就已经达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洲的金融经济问题,以及欧洲的回旋余地(关于社会经济野心),这个“体系”编纂了跨大西洋的现实,即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的货币秩序(而美元又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汇率与黄金挂钩)。
因此,欧洲一体化成为194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追求弹性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一个要素,并导致了一个国际协调的体系,约翰·鲁格(John Ruggie)在1982年将其描述为“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政权”,鲁格将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概念建立在双重主张之上。
一方面,他解释说,获得认可的“多边秩序”反映了美国资本的侵略性(特别是在贸易方面)。
另一方面,他强调“多边主义和对国内稳定的追求是相互结合的,甚至相互制约的”,这“反映了工业世界已经转向的一系列社会目标的共同合法性”,这种争取共同社会目标的运动,如充分就业和不平等作斗争,始于大萧条时期,并在1940年代初获得了势头,历史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发生变化。

尽管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学者从未真正参与欧洲一体化现象,但一体化过程确实构成了鲁格战后“工业世界”美国和平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一现状又是柔和的。
换句话说:在1950年欧洲一体化起飞的时刻,任何可行的欧洲一体化模式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嵌套在已经存在的跨大西洋制度结构中。
为战后多边主义制定的宏伟设计,在 1940 年代主要是英美政策界内的设计,其中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詹姆斯·米德、保罗·霍夫曼、罗伯特·特里芬和让·莫内等关键人物。
首先,看待这些这些计划,需要先看它们的目标可能有多深远,要知道其计划仍然嵌套在资本主义和宪政民主的制度形式中,一切都是关于重新调整,而不是革命。
其次,参与其中的政策工程师坚定地致力于在国际上分担社会责任,并促进跨国界的合作(以软化这些边界,以及相互联系的强化身份边界),换言之:它本身就是一个目标,即使主导国内议程的政策如重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社会凝聚力等“多边化”。
再次,西方在制定计划过程中的联合合作,努力集中在非常适合非政治规划的技术政策领域:贸易、金融和货币治理,这些方面也在日后变得越发壮大。
最后,战后资本主义秩序的所有宏伟设计都有一个首要和总体目标——稳定,而规划和多边主义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新工具。
此外,这种宏伟的设计与另一种吸引人的前景有关,它似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使跨大西洋世界摆脱了自由贸易市场的教条主义,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1944年出版)中所解释的那样:这种虚假的,最终具有破坏性的“自我调节市场”的“乌托邦”,对波兰尼来说,金本位制及其不可避免的衰落(以及它所执行的通货紧缩的国内纪律)代表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陷入的“灾难的近因”。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状?
原因是各国政府一直在徒劳地寻求在国际贸易固有的不稳定,而又能存在于现实中的稳定,最初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的时候,这引发了一系列无望的努力,即通过稳定汇率来稳定世界贸易,其基础是自我调节市场的虚构,也就是号称为“跨越大西洋的专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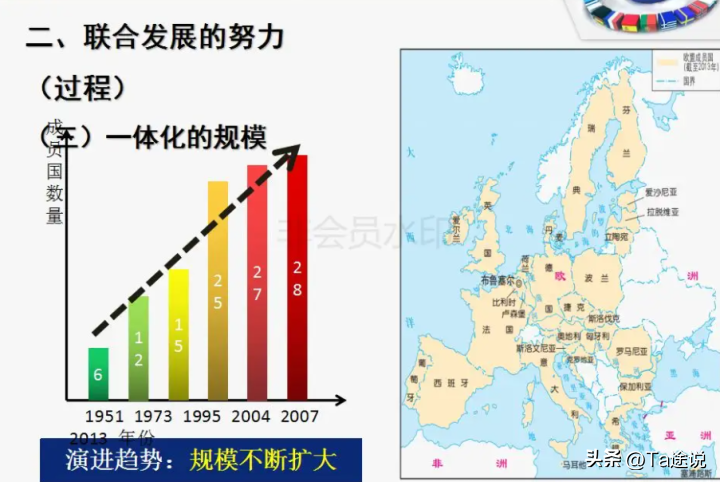
根据波兰尼的说法,这种“非系统”带来的与它的设计目的完全相反:它引发了大萧条,随后使美国在 1933 年摆脱了黄金,使金本位制陷入混乱,要知道逐渐恢复金本位制一直是“世界团结的象征”。
通过提出这一论点,波兰尼强调了一个总体趋势,这种趋势在学术界同行和政治家族以及政策精英中广泛存在:“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发展,在这种发展下,社会高于经济体制的制度得到了保障......市场体系将不再自我调节,即使在原则上也是如此。”
从这种政治经济角度出发,波兰尼得出结论:“这种情况很可能对外交政策提出两个明显不相容的要求,它需要友好国家之间比十九世纪主权下所能想象的更密切的合作,同时规范市场的存在将使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进行外部干预。”
波兰尼看到的西方世界正在出现这种变化,在那里,“政府的经济合作和随意组织国家生活的自由”作为新制度的组成部分彼此相邻存在。
其中“联邦”这一个想法被认为是集中化和统一的噩梦在市场经济和金本位制下,很可能成为实现与国内自由的有效合作的多种方式之一。
正是在这里,必须寻求战后资本主义大逃亡的途径,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程和它们之间的多边合作方面,跨大西洋决策者的绝大多数与波兰尼完全一致。
1944年,也就是波兰尼的书出版的那一年发生了变化,波兰尼在他的全面分析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上显然是错误的:对货币稳定性的执着比战争更持久。
这与对稳定的压倒性渴望有关,事实上,当涉及到现实生活中的政策来安抚这种愿望时,战后计划根本没有那么创新,西方蓝图的前沿人物沉迷于大西洋对稳定汇率的执着,就像金本位制的政策热点所做的那样,在许多人眼中,稳定的货币只是“政治理性的试金石”,而其所发生的变化也主要服务于政治方面。
这种变化相对较快的时候,战后世界在金融经济事务中的多边宏伟设计几乎完全集中在汇率稳定上,这被认为是任何可持续秩序的必要条件,从体制上界定这个世界的唯一最重要的努力是布雷顿森林会议,正是这场会议促进了这种变化的发展,所以这是一项完全旨在稳定汇率的工作。

无论是协调福利国家政策的趋势,还是普遍坚持的多边努力,以服从货币到黄金逻辑(支配着灾难性的战争内部)都被牢牢地推到了幕后,且鲜为人知,但是总有人没有忘记这个方面。
然而,稳定似乎是一个多方面的概念,远非易事。就国际收支平衡而言,内部、国内和社会经济稳定(充分就业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威胁到国际经济的外部稳定,与这个基本问题相关的是,人们深切担心助长大萧条的毁灭性(民族主义)经济活力会重演,许多人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遏制与这种历史性的崩溃螺旋有关的现象,例如竞争性贬值和通货紧缩。
关键问题是:如何同时提供国内社会经济确定性和公平性、国际收支稳定性以及货币和金融确定性?
最初,新思维最终导致对金本位制旧世界的无节制攻击,即使不太清楚替代方案是什么。寻求救赎实在是太引人入胜了,对旧制度的谴责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在旧制度中,对汇率的捍卫压倒了对国内充分就业政策的追求,这显然是错误的。
当实际计划起草和国际谈判的现实开始时,与最初对变革的热情相比,事情变得相当温和。
这使金融经济和货币治理成为国际合作的核心,并为战后西方的多边机构的建设设定了界限,这也就是历史对战后西方的机构建设所造成的一种相对消极的影响。

